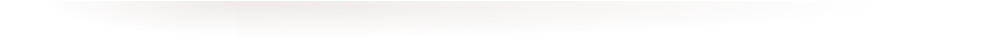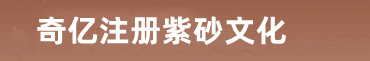首页(盘古注册)首页,瓷的名品,长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的珍视,成为富有人文内涵的“玩物”。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将紫砂器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视野。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紫砂器在窑址、墓葬、城址、沉船等遗迹中的考古发现,重点分析了考古学方法和资料对于紫砂年代判定、品种、工艺、艺术、营销范围等方面研究所起到的推进作用。但就目前来说,紫砂器在陶瓷考古的工作中,无论是资料的重视程度,还是“操作链”式的研究理念都略显不足,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紫砂器是继新石器时代彩陶、秦汉陶塑、“唐三彩”及长期传承的铅釉陶器之后的陶艺珍品,肇始于江南,是实用器与艺术品的完美结合[1]。紫砂器产生于江苏西南端的宜兴市(古称“荆溪”,秦改“阳羡”,晋易“义兴”,宋改宜兴),兴盛于明清,精美器物与著名工匠的紧密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名器与名匠的效应使其声名大振。据文献记载,紫砂器的制作和研究在明代便已开始。明崇祯年间,周高起撰《阳羡茗壶系》分其器型、究其工艺、赞大家之巧工[2]。清乾隆时,吴骞撰《阳羡名陶录》[3],多以诗歌的形式赞扬紫砂器的精工与优雅。
20世纪70年代之前,相关研究主要依据传世品和古代文献,无法对紫砂及其人文因素发展等问题做深入探究,使得紫砂器的研究一直停滞在简单的“纸上研究”。紫砂器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正式展开,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窑址的试掘和2005年宜兴蜀山窑址的考古发掘是紫砂考古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对紫砂开展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6年之前,是萌芽时期。伴随着各地的基建,在西安、杭州等地发掘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少量日用紫砂器。南京市中华门马家山吴经墓是此期唯一出土紫砂器的高等级纪年墓葬。这一阶段没有任何针对紫砂的主动性考古工作,零星发现的紫砂器也是在清理其他遗迹时偶然所得。
2.第二阶段,1976年—2005年,是紫砂考古和研究的初创时期。通过对羊角山紫砂窑址的调查和试掘,首次在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紫砂器,为研究其烧造历史及工艺特征提供了新资料。此阶段在沉船、遗址、墓葬、窖藏等考古遗迹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紫砂器。无锡华师伊夫妇墓、漳浦蓝国戚墓、赵西漳墓、卢维桢夫妇墓等墓葬中发现了带有时大彬、王南林、陈鸣远等名家款识的紫砂器。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万历号、迪沙如号(Desaru)、泰兴号(Tek Sing)等沉船中也出水了数以千计的日用紫砂器。这些发现使学界认识到可以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紫砂进行诸多方面的研究,突破仅依靠传世品和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如对紫砂产生时间的判定,不同时期的器物组合、工艺和艺术特征等,由此开启了紫砂研究的新纪元。
3.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是紫砂考古蓬勃发展的时期。特点是开始了主动性的窑址发掘,在其他考古遗迹的发掘工作中,对紫砂器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研究中多学科交叉,尤其是科技方法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对宜兴蜀山窑址的发掘,出土了3万多件紫砂器,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对紫砂窑址进行的正式发掘。此外,在河南开封明周王府和江苏泗州城等遗址也发掘出土了一些紫砂器具。这一阶段紫砂考古表现为从其他考古遗迹中间接获取资料,变为主动地对紫砂窑址进行发掘。尽管发掘报告至今未能刊布,但已披露的资料对紫砂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冯先铭[4]、刘汝醴[5]、顾景舟等学者先后到宜兴蜀山、鼎山考察,确认了紫砂器的生产地点就在这两地及附近区域。1976年,在宜兴红旗陶瓷厂基建中,发现了羊角山窑址,清理了一条宽1米、长10余米的小龙窑及窑业堆积。出土器物以壶、罐类为主。通过此次考古出土的大量紫砂器,确认了宜兴丁山为早期紫砂器的重要生产地点[6]。2005年11月至2007年7月,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等单位对位于宜兴市丁蜀镇的蜀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7],发掘面积700平方米,揭露了窑炉遗迹10处,出土明末清初至建国初期的紫砂、钧釉陶器及其他日用陶瓷标本3万余件[8]。通过此次发掘,对在蜀山窑址开展了分期研究,明确了宜兴紫砂器的创始时间,时代特征和工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出土紫砂器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靠近紫砂产地的周边城市,如徐州、扬州、无锡、宜兴、南京等。出土器物以铫子、花盆、匜口罐等日常用器为主,兼有砚滴等文房用具。其中紫砂器的重要发现主要有3次,2005年徐州市大同路南侧徐州卫所遗址出土两件明晚期紫砂穿心铫[9];2014年开封市新街口明代周王府遗址发掘出土明晚期紫砂罐、盖壶、荷叶形紫砂杯、月牙形紫砂砚滴各1件[10];2011年至2014年,江苏省盱眙县泗州城遗址发掘出土30余件紫砂器,时代不晚于1680年,器类有茶壶、罐、花盆等[11]。
此外,1955年西安东郊新安砖厂扩建时出土1件清代“荆溪徐渭廷制”款汉方壶[12]。1959年杭州市半山机械厂出土3件乾隆时期紫砂器[13]。1965年镇江市出土明代和清代球形壶各1件。1972年南京市栖霞张化村出土1件清道光九年“杨彭年制”款方柱础式紫砂胎锡壶。1973年镇江市一中弹簧厂出土1件“邵文茂制”紫砂带盖钵。1975年和1976年扬州市马庄和缪庄分别出土明代紫砂碟和紫砂方罐。1978年句容市春城镇村民挖出四系紫砂壶1件[14]。1989年淮安市文管局在板闸镇板闸村中征集到出土的清嘉庆“王南林制”款紫砂壶和清晚期竹节形软提梁壶[15]。1989年泰州市东郊迎春住宅小区工地出土1件紫砂绞胎壶[16]。1995年安徽省芜湖市曾家塘出土1件“惠孟臣制”紫砂茗壶残器[17]。1999年扬州唐城考古队在扬州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南侧发掘明代灰坑1处,出土2件紫砂匜口罐[18]。2004年江苏扬州市中医院基建工地出土1件“张君德制”紫砂盖钵[19]。
1991年无锡市南禅寺发现10余口明清时期的土井,出土鼓墩形四系紫砂壶、带把带流紫砂罐、圆形紫砂小壶各1件[20]。1999年发掘扬州市大东门街东侧的六口古井,出土了较多的紫砂器,包括40件紫砂圆壶、1件球形壶、2件“荆溪所制”款汉方壶、6件汤匙、5件小碟[21]。2002年金沙市金沙广场水井出土明嘉靖紫砂提梁壶、明正德至万历紫砂匜口罐、明紫砂花盆各1件[22]。2010年宜兴市东郊溪隐村徐氏宗祠东侧古井,出土紫砂提梁壶3件、匜口罐1件、酱釉紫砂罐1件、酱釉紫砂壶3件、紫砂小缸1件、穿心铫残件2件[23]。2014年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古井J15出土了紫砂筒形器2件、提梁壶2件、紫砂壶盖和壶底各1件[24];J26出土了1件紫砂筒形提梁壶[25]。
墓葬出土的紫砂器数量较少,但较完整,断代意义重要。出土紫砂器的墓葬有19座,分布于江苏、上海、福建、陕西、山西、河北、北京等地。部分高等级墓葬带有纪年,出土紫砂器兼有实用器和陈设器,且多印或暗刻名家款。平民墓出土的紫砂器多为铫、茶叶罐等日用紫砂器。
1996年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嘉靖十二年(1533年)太监吴经墓出土1件提梁紫砂壶,是迄今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紫砂器[26]。1968年扬州丁沟公社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墓出土1件“大彬”款六方壶[27]。1974年河北正定县顺治七年(1650年)梁维本墓出土了明万历“陈用卿制”款紫砂壶[28]。1975年山西襄汾县清嘉庆五年(1800年)刘文虎墓出土1件嘉庆粉彩山水纹紫砂壶[29]。1975年扬州郑王庄万历四十四年曹氏墓出土1件“大彬”款六方壶[30]。1979年上海金山县清嘉庆八年(1803年)王坫山墓出土1件陈曼生自铭款紫砂竹节壶[31]。1984年江苏省无锡县明崇祯二年(1629年)华师伊夫妇墓出土1件“大彬”款紫砂壶[32]。1986年淮安市河下镇王光熙墓出土2件紫砂壶,其中1件为“彭年”款陈曼生制乳鼎壶,另一件为“大彬”款,墓葬时代为清代前期[33]。1986年泰州西郊明末清初土坑墓出土1件紫砂茶叶罐[34]。1987年山西省晋城市泽川县大阳镇明崇祯五年(1632年)张光奎墓出土1件“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夏日时大彬制”款紫砂壶[35]。1987年福建漳浦县盘陀乡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卢维桢夫妇合葬墓出土1件“时大彬制”款紫砂壶[36]。1987年陕西省延安市柳林乡明墓出土1件“以饪养浩然大彬”款提梁壶[37]。1990年福建漳浦县南坑村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蓝国戚墓出土“鸣远仿古”款紫砂壶1件[38]。1995年湖北武汉市明崇祯楚藩郡王墓出土“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秋,时大彬制”款紫砂罐[39]。1996年常州市潞城镇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墓出土1件六边形紫砂罐[40]。2002年北京工商大学操场明万历十年(1582年)御用监太监赵西漳墓出土2件紫砂壶和4件紫砂套杯[41]。2007年扬州市瘦西湖万花园明代墓葬出土2件紫砂小碟[42]。2009年南京市板仓街明墓出土1件紫砂铫[43]。
窖藏出土紫砂器仅见1例。1986年绵阳市博物馆在红星街发掘一处明代窖藏,出土1件“大彬”款紫砂壶,是紫砂器流布四川的重要证据[44]。
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在许多沉船中都出水了紫砂器,最早的发现是1981年法国水下考古部在法国剌培鲁斯航海船队水下遗址(Lapérouse)的发掘,共出水77片紫砂壶残片,其中以乾隆六角瓜棱茶壶最为典型[45]。1981年至2008年间,约有10艘沉船出水紫砂器,按照船沉没时间顺序分别为:马来西亚西海岸发现的万历号沉船(明天启,约1625年)[46]、福建东山岛东古湾沉船(清康熙,约1676年前后)[47]、越南头顿号沉船(Con Dao)(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48]、南非桌湾奥斯特兰号沉船(Oosterland)(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49]、本那勃号沉船(Bennebroek)(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50]、剌培鲁斯航海船队的“指南针号”沉船(La Boussole)和“天体仪号”沉船(L’Astrolabe)(乾隆年间)[51]、印度尼西亚哥德马尔森号沉船(乾隆十七年,1752年)[52]、印度尼西亚泰兴号沉船(道光二年,1822年)[53]、马来西亚柔佛州迪沙如号沉船(道光,约1845年)[54]、浙江宁波小白礁Ⅰ号沉船(道光年间)等[55]。从沉船的时代分布看,紫砂器于明末时开始少量外销,康熙年间极盛,持续到晚清时期。
第一阶段。1980年之前,以顾景舟等当代工匠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刘汝醴、宜兴市韩其楼等学者的研究为主。研究对象主要是传世紫砂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近代紫砂器的美学特征、制作工艺、造型及对紫砂器的简单分类和定义。
第二阶段。1980—2005年,随着羊角山窑址资料的公开,吴经墓等纪年墓葬出土紫砂器的发现,考古资料开始被运用到紫砂研究中。通过对出土器、传世品的对比研究,获得了对馆藏器物年代和工艺发展阶段的认识。
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紫砂研究快速发展时期。随着蜀山窑址的发掘,遗址、墓葬、沉船出土资料的大量积累,为研究紫砂的制作方式、工艺发展、流通、使用、鉴赏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代紫砂名匠通过对蜀山窑址出土紫砂器的观摩和学习,将古代工艺技术融入到当代紫砂器的制造当中,兴起一股紫砂“仿古风”。
1948年《新中华》杂志刊布了清代紫砂名家陈鸣远紫砂壶图录[56]。1979年韩其楼对紫砂器进行了简单的造型分类和美学分析[57]。1978年《紫砂陶器造型》一书,详细介绍了馆藏紫砂器的泥料、成型工艺、造型分类、制作手法等[58];1982年出版的《宜兴陶器图谱》对宜兴紫砂进行了类型学的分类和整理[59]。20世纪80—90年代,由于考古出土的带名家款识的紫砂器不仅可与文献记载对应,也可与传世品相参照,学者们集中对出土和传世的时大彬、供春、陈曼生、陈鸣远等带名家款识的紫砂壶进行了研究。如蒋华介绍并研究了江都明墓出土时大彬六方紫砂壶[60]。贺盘发介绍并研究了无锡县出土的时大彬款紫砂茗壶[61]。金琦研究了曼生壶的款识和造型特征[62]。刘汝醴对曼生壶的款印、制作工匠、制作年代、造型和工艺特征进行了分类和总结[63]。王正书认为清代“曼生壶”的制作时间为嘉庆八年到二十一年左右[64]。李久芳将明代剔红漆器与同时期大彬壶进行了工艺特征对比[65]。宋伯胤对明卢维珍夫妇墓、曹氏墓、华师伊墓出土的3件时大彬作紫砂壶的造型和技艺进行了分析[66]。在名家名品的汇集研究中逐渐将紫砂引入了系统研究的范畴。
进入21世纪,叶佩兰、万新华分别对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进行了研究[67];徐秀棠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总结了历代紫砂器的发展脉络[68]。张卉研究了紫砂器的制作工艺、造型、原料及品类等方面的发展特点[69]。宋伯胤总结了明清各朝紫砂名家的壶艺特征,并探讨了各时期紫砂名家与文人的交往对紫砂壶造型转变的影响[70]。朱泽伟对蜀山窑址中出土的紫砂器进行了泥料特征、装饰工艺、重要烧成工艺方面的探究。吴光荣等对蜀山窑址出土的标本进行了探讨,指出明代末期至清代中期制作工艺出现了较大的改进[71]。可以看到,学者们在着眼于真伪判定,精品鉴赏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紫砂的工艺发展脉络和艺术特征。
近些年来,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紫砂器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埃娃·施拖波(Eva Str·ber)介绍了欧洲著名收藏家奥古斯塔(Augusta)所藏宜兴瓷器和紫砂器的情况[72]。谢瑞华介绍了美国西海岸宜收藏兴紫砂的概况[73]。刘明倩介绍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120余件宜兴紫砂的装饰工艺[74]。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对大英博物馆自1876年以来收藏的紫砂器进行了介绍与研究[75]。柯玫瑰(Rose Kerr)对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的紫砂藏品进行了介绍与研究[76]。
基于羊角山紫砂窑址的发掘资料,孙荆[77]、韩人杰[78]、陈显求[79]等对紫砂泥的地质特征,矿体形状,原料制备工艺及成型工艺做了较为详细的理化分析。李家治等将清代葛窑宜均器同历代紫砂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梳理了紫砂器工艺技术的发展、装饰方法的演变[80];张茂林等对蜀山窑址出土的明晚期至晚清、民国时期的紫砂样本做了微量元素检测,获得了历代紫砂器的化学组成特征[81];吴隽等对31件具有代表性的紫砂器标本进行了元素组成和性能结构的分析[82]。
随着沉船出水紫砂器和海外发现的不断增多,外销研究逐渐成为紫砂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施云乔等讨论了紫砂器从传入到开始在欧洲各地进行仿造的历程[83]。帕特里斯·万福莱(Patrice Valfre)第一次将全球贸易的视野纳入宜兴紫砂的研究中,介绍了紫砂器贸易及欧洲收藏、仿烧紫砂壶的情况[84]。黄健亮以欧洲皇室贵族收藏的紫砂为出发点,探究了荷兰、英国、德国等地仿烧宜兴紫砂器的特征异同[85]。林业强将沉船出水紫砂器分为三大类——船员自用品、船员私货、外销货物,为研究外销紫砂的运输途径和器型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86]。黎淑仪探讨了外销紫砂器对东南亚、欧洲市场的文化促进以及德国麦森瓷厂、荷兰代尔夫特仿烧紫砂器的特征[87]。黄巍锋总结了外销紫砂壶对东洋瓷业的影响,指出宜兴紫砂壶于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受到日本消费者的喜爱,日本万古烧窑口于元文元年(1736年)也开始仿烧紫砂壶[88]。王亮钧将日本18处、琉球群岛26处遗址出土的紫砂器同沉船出水、中国遗址中出土的宜兴紫砂器进行对比研究[89]。时至今日,学者们对外销紫砂的研究已经从器物发展史的角度逐渐扩大到全球贸易、经济、文化史的研究视角。
紫砂与明代以降出现的冲泡茶的茶饮文化紧密相联,许多学者从茶文化和审美鉴赏的角度来阐释紫砂器的文化内涵,划分出了商品类型壶、文人类型壶、外销类型壶和宫廷类型壶等几类[90]。指出明清时期饮茶风尚的盛行、士人阶层的喜爱与推动、匠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人与匠人的交互影响等是紫砂器在民间快速兴盛的原因[91]。
由于考古发现数量有限,以及对文献记载、工艺发展等方面的理解不同,长期以来,人们对紫砂器的创烧时间,紫砂器的定义,宜均与紫砂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一些学术争论。
关于紫砂器的创烧时间有宋代说和明代说两种观点。宋代说以贺盘发为代表,根据羊角山紫砂窑址考古出土的紫砂器残片,推断烧造年代为“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92]。支持宋代说的学者有刘汝醴[93]、韩其楼[94]、蒋赞初[95]、潘春芳[96]、汪庆正[97]、杨振亚等[98]。宋伯胤对此观点有所保留,认为紫砂器是宋代中期到明代早期缓慢发展的一个过程,羊角山窑址仅为明代民间紫砂窑场[99]。
袁志洪否定了宋代说[100],李广宁、张浦生认同此观点[101]。明代说观点主要认为,羊角山紫砂窑址并非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少量标本不足以证明紫砂起源于宋代,宋代诗文中的“紫瓯”和“紫泥”应为紫黑色茶盏或是粗泥[102]。而明嘉靖十二年吴经墓出土的提梁紫砂壶是最早的考古学证据。蜀山窑址的发掘成为对紫砂创烧年代认识的重要节点,愈来愈多的学者认同紫砂器创烧于明代。杭涛认定紫砂器起源于明代晚期[103]。黄兴南[104]、陆明华等均认同明代说[105]。尽管此后仍有少量学者坚持宋代说,不过并未能提供可靠的实物证据[106]。
对于紫砂器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狭义的界定,即明代中晚期利用宜兴紫砂泥通过拍片镶接法制成的饮茶器、文房器、陈设器等是紫砂陶器。广义的紫砂器认为在制陶中发现并利用紫砂泥制成的符合地质学紫砂特性的陶器[107]。杭涛认为应将不同时期人们对紫砂器的认识程度作为考察器物是否为紫砂器的衡量标准[108]。
产生这一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对紫砂和宜钧的定义不完全一致,因此造成定义范围上的混淆和不一致。第二,宜钧器同紫砂器一样,传世品多于出土器,考古资料较少,难以形成系统的对比和研究。日本学者小森忍基于对宜兴窑的实地考察,最先将欧窑、蜀山窑、鼎山窑划入宜兴窑系[109]。《中国陶瓷史》一书[110]和叶喆民将宜钧划为宜兴紫砂器的一个品类[111]。由于在蜀山和羊角山两处窑址中都同时出土紫砂和宜钧器,认为二者同根同源[112]。随着科技考古的深入,有学者对羊角山紫砂窑址出土的历代紫砂陶[113],宜钧及传世紫砂器的化学成分特征进行了研究[114],从胎的化学组成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王朔飞通过对宜钧的分期研究,证明清中期“葛窑”的诞生标志着宜钧正式从紫砂器中脱离,成为一类独立的旁支产品[115]。事实上,蜀山窑的发掘资料为我们呈现了两类宜钧产品,一类是宜兴生产的瓷胎钧釉器物[116],另一类是在紫砂器物上施钧釉的器物,应该属于釉陶的范畴。没有注意这一区别的研究都难免片面。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紫砂器开始在不同的考古遗迹中出土;又因为受到陶瓷考古的影响,研究者关注到了生产地点——窑址的资料和其他出土资料,使得紫砂进入了考古学的视野。随着对紫砂研究的日渐深入,对紫砂概念的界定,创始的时间和发展脉络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同时,根据紫砂的特点,对其使用功能和发展变化,对著名工匠的作品和特点,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制约研究深化的问题,第一,窑址资料主要是早年简单的调查和不规范的试掘,无法获得可靠的地层关系,也就无法获得准确的年代信息。对紫砂发展变化的研究还主要是从传世品和器物风格排比展开的。第二,其他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紫砂器,仅占极小的比例,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紫砂器从其产生伊始,就与其使用价值之外因艺术特点和工匠的名声形成的价值溢出,进而逐步形成的收藏观念密切相关,研究的视角大多纠结于一些细节。问题是在考古学方法引入以后,并未能从研究的视角上提升紫砂的研究。从陶瓷考古研究的角度看,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
[1][22][75][76]龚良.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联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4]冯先铭.有关钧窑诸问题[C]//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6][92]宜兴陶瓷公司《陶瓷史》编写组.宜兴羊角山古窑址调查简报[C]//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59-63.
[7]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宜兴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2.
[8]杭涛,马永强.宜兴蜀山窑址的发掘[J].故宫文物月刊,2008(302).
[9]孙爱芹,赵赟.徐州卫出土最早的紫砂穿心铫[N].中国文物报,2008-6-11-5.
[10]王三营等.河南开封新街口明周王府官署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7(3).
[11]张雪菲.江苏盱眙泗州城遗址出土紫砂器研究[J].东南文化,2016(3).
[12]王晶晶,杨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紫砂壶赏析[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7(24).
[13]阮平尔.杭州乾隆时期墓出土的紫砂器[J].东南文化,1988(2).
[14][30]刘丽文.镇江博物馆藏明清陶瓷茶具[J].收藏,2014(7).作为藏品介绍,这些器物只有出土地点,失去了其他考古信息。
[15]张浦生.紫砂古韵魅力长存——介绍一批墓葬出土明清宜兴紫砂茗壶资料[J].东方博物,1998(2).
[16]康羽荻.绞胎技法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应用[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9]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著.广陵遗珍[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227.
[20]朱建新.无锡南禅寺出土的明代紫砂器[J].文物,2002(4).
[21][42]薛炳宏等.扬州今年出土的宜兴紫砂器具[C]//宜兴窑古代陶瓷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宜兴: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2014:142.
[23]黄兴南等.宜兴溪隐古井出土宜兴窑陶器[C]//紫泥沉香·2015宜兴紫砂学术研讨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27-234.
[24]祁海宁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J15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6).
[25]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大报恩寺遗址J26发掘简报[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8).
[26]徐佩佩.明御用监太监吴经墓出土文物的一些考证[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19).
[27][60]蒋华.江都明墓出土时大彬六方紫砂壶[J].文物,1982(6).
[28]刘友恒.正定县梁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J].文物春秋,1995(1).
[29]陶富海.记一件清嘉庆粉彩山水紫砂壶[J].文物,1985(12).
[31][64]王正书.从出土实物谈陈曼生和他的“曼生壶”[J].文物,1985(12).
[32]冯普仁,吕兴元.江苏无锡县明华师伊夫妇墓[J].文物,1989(7).
[33][68]徐秀棠.紫砂工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27.
[34]潘耀.紫泥新品泛春华——明末清初紫砂器探微[J].东方收藏,2012(4).
[35]李建生,张广善.“丁未夏日时大彬制”款紫砂壶[J].上海文博论丛,2004(2).
[36]王文径.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墓[J].东南文化,1989(3).
[38]王文径.清蓝国威墓和陈鸣远制紫砂壶[J].东南文化,1991(Z1).
[39]祁金刚等.武汉江夏流芳四股山明墓发掘简报[J].武汉文博,2010(4).
[40]唐星良,葛君凯.常州市区明墓群的发掘[J].东南文化,2003(11).
[4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
[43]王志高等.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明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8(4).
[44]何志国等.绵阳市红星街出土明代窖藏[J].四川文物,1990(2).
[45][51]赵冰.浅析法国18世纪剌培鲁斯船队水、陆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1).
[47]陈立群. 福建东山岛冬古沉船遗物研究[J] . 闽台文化交流,2007 (1) .
[55]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57]韩其楼.紫泥新品泛春华——宜兴的紫砂陶茶具[J].文物,1979(5).
[58]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编.紫砂陶器造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78.
[59]詹勋华编.宜兴陶器图谱[M].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2(1).
[61]贺盘发.无锡县发现珍贵的时大彬紫砂名壶[J].江苏陶瓷,1984(2).
[62]金琦.紫砂名品——曼生壶[J].文博通讯(江苏),1984(4).
[63]刘汝醴.清代紫砂第一名手陈鸣远[J].美术家(香港),1984(39).
[65]李久芳.明代剔红漆器和时大彬紫砂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4).
[66][99]宋伯胤.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修订本)[M].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2005.
[67]叶佩兰.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J].收藏家,2001(12);万新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紫砂器[J].收藏家,2004(1).
[69]张卉.中国古代陶器设计艺术发展源流[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
[70]宋伯胤等.中国紫砂收藏鉴赏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1]吴光荣等.管窥明清时期宜兴蜀山窑址出土紫砂壶标本制作工艺之演变[C]//紫泥沉香·2015宜兴紫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2-41.
[72]埃娃·施拖波.强人奥古斯塔收藏中的宜兴瓷及德化瓷以及欧洲瓷器的发明[C]//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73]谢瑞华.美国西海岸宜兴紫砂收藏概况[C]//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281-294.
[74]刘明倩.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C].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103-108.
[77][113]孙荆,谷祖俊,阮美玲.羊角山古窑紫砂残片的显微结构[J].中国陶瓷,1984(2).
[78]韩人杰,叶龙耕,贺盘发,李昌鸿,高海庚.宜兴紫砂陶的生产工艺特点和显微结构[J].硅酸盐,1981(4).
[79][114]陈显求,黄瑞福,陈士萍,朱肇春,叶龙耕.清代葛窑宜均陶的化学组成和分相结构[J].硅酸盐学报,1988(6).
[80]李家治编.中国陶瓷技术史·陶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1]张茂林,李其江,吴军明.宜兴蜀山窑址出土历代紫砂陶的化学组成特征研究[J].中国陶瓷,2016.
[82]吴隽,吴军明,张茂林,李其江,李家治,邓译群.中国历代宜兴紫砂器的元素组成和性能结构探析[C]//紫泥沉香·2015宜兴紫砂学术研讨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42-53.
[83]施云乔等.宜兴紫砂陶的海外效应[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8.
[84]帕特里斯·万福莱著,施云乔译.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
[85]黄健亮.宜兴紫砂器在欧洲的文化历程[J].东南文化,2016(3).
[86]林业强.紫泥沉浮:沉船所载宜兴砂壶[C]//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87]黎淑仪.宜兴紫砂之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J].东南文化,2009(2).
[88]黄巍锋.古外销紫砂壶使用情境及造物特征的跨文化研究[D].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89]王亮钧.日本出土的紫砂器及其相关问题[J].故宫学术季刊,2018(35).
[90]霍华.关于紫砂壶的三点思考[C]//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91]王子怡.中日陶瓷茶器文化研究[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王叶菁.紫砂壶在明代江南的兴起与传播[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士论文,2014;余同元.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1520-1920)[D].复旦大学硕士学士论文,2005;曹清.陈洪绶的隐逸之符——明季江南文化视野下的阳羡茗壶[C]//紫泥沉香·2015宜兴紫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64-278.
[95]蒋赞初.宜兴紫砂的历史与现状[C]//紫砂春秋.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
[96]潘春芳,贺盘发.我国紫砂器的起源和发展[J].江苏陶瓷,1980(2).
[97]汪庆正.上海博物馆藏宜兴陶器[C]//宜兴陶艺——茶具文物馆罗贵祥珍藏.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1990:82.
[98]杨振亚.宜兴紫砂器源于宋代论[J].江苏陶瓷,1994(02):42-46.
[100]袁志洪等.紫砂茗壶起源考述[J].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135-140.
[102]袁志洪.梅尧臣诗“紫泥”“砂婴”辨析——再述宋代无紫砂[J].无锡文博,2001(3).
[103][108]杭涛.紫砂器起源的几个问题[C]//高晓然主编.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153-160.
[104]黄兴南.宜兴窑古代陶瓷概述[C]//宜兴窑古代陶瓷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宜兴: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2014:27-29.
[105]陆明华.宜兴紫砂器起源与明代名家茗壶研究[J].东南文化,2016(03).
[106]贺云翱.宜兴紫砂陶传统工艺综述[C]//宜兴窑古代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宜兴: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2014:85-86.
[107]孙振等.早期紫砂胎器初探——记一件紫砂胎黑釉壶[C]//宜兴窑古代陶瓷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宜兴: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2014:97-103.
[109]小森忍.支那古陶磁の話[M].日本:东京市商务印刷所,1926.
[110]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111]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5]王朔飞.明清宜均陶器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
[116]这类器物实际上是明代十分流行的胎体不很白的普通瓷器,即西方所说的Stoneware的胎,不同于白胎的瓷器和陶胎。这是中国境内普遍生产的瓷器品类。
(作者:高宪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朔飞 英国杜伦大学;秦大树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通讯作者];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6期)
公司地址:山东省威海市奇亿紫砂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15232077821
传真:400-822-4455
邮箱:595588519@qq.com
集团网址:http://www.qzqsjy.com/